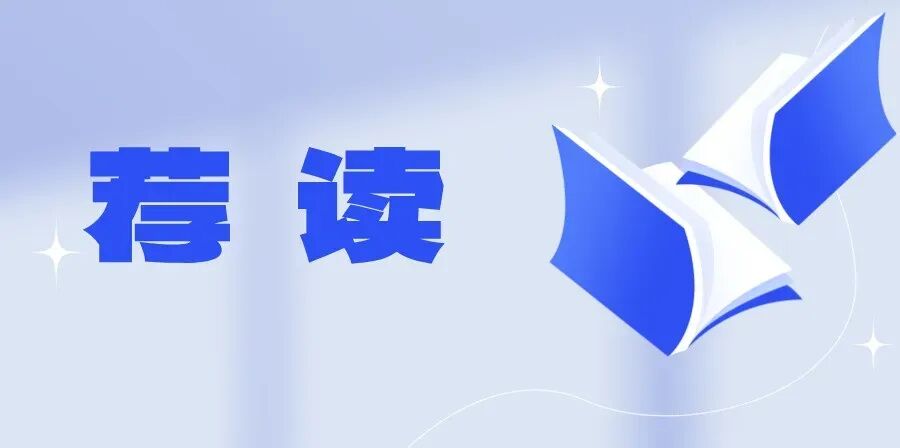
(一)深化学理研究、形成统一的概念认知体系
基于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信用治理已逐步成为与道德、法律并重的新的社会治理机制,并且在某些场景下已成为更有效的治理机制。建议把社会信用治理视为新的交叉学科,组织信用、法律、社会、经济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联合开展研究。同时,在信用治理研究和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作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信用治理理论。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诚信、信用、征信等重要概念。建议采用“公共信用”“市场信用”“社会信用”“经济信用”等有明显区分度的表述,避免将社会诚信合规体系与经济金融信用体系相混淆。对于地方和行业的各类信用法规、文件中模糊不清的信用概念,应予以统一规范。
(二)加快信用法治建设、杜绝信用泛化现象
要解决目前信用建设中存在的信用泛化和信用修复难等问题,根本途径是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建议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于“健全市场化信用机制、促进和优化法律实施、保障和强化法律实施”三个方面,而不应赋予“道德强制”方面的功能。在法律文本中,与其采用宏大且内涵不明确的目标描述,不如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予以精准表达,从而更好地指引制度设计与具体实践。“健全市场化信用机制”“促进和优化法律实施”“保障和强化法律实施”可分别表述为“健全市场化征信体系、促进信用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信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基础作用”和“遏制重大违法行为”等。
要严格依法依规采集公共信用信息、实施失信惩戒。在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和失信惩戒措施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类公共信用信息的纳入标准和评价标准。例如,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记录不宜纳入公共信用记录;对于失信主体,应依据其主观恶意程度、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及违法失信情节的不同进行适当的分类;对于偶发的、非故意的失信行为不宜列入严重失信名单。在信用的惩戒措施方面,应在信用信息的保存期限、信用信息的披露公示范围、是否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奖惩等方面,设置不同的规则。应统一各部门的信用修复规则,推广在线修复等便利化修复措施,实现同一不良信用记录在一个部门修复完成后,其他部门予以同时自动修复等。
(三)发挥政务诚信引领带动作用
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着力解决“新官不理旧账”、损害市场公平交易、危害企业利益等政务失信行为,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和惩戒制度,将机关、事业单位的违约毁约、拖欠账款、拒不履行司法裁判等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长效机制,依法依规加大对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力度。建议加快建立公共部门和公务员个人的诚信档案,引入第三方政务诚信评价机制,并将诚信档案和评价结果依法进行公示,接受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和社会监督。
(四)健全商务信用体系、大力发展信用经济
一是将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治范围,适时出台专门法律,完善法规执行机制。强化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信息披露和信用惩戒。规范分包合同,防止大企业利用合同侵害中小企业利益。
二是发挥信用在扩大交易规模、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的作用,鼓励开展信用销售和信用消费,发展高水平的信用经济。
三是完善中小微企业征信、增信、风险分担和风险补偿机制,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解决好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问题,加强公共信用信息与金融信用信息融合,通过多维度大数据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精准信用画像,大力发展信用融资。
四是高质量发展信用服务行业(征信、信用保险保付代理、信用担保、商账追收等),通过市场化、数字化手段盘活企业应收账款。
五是加强行业自律组织信用管理机制建设,建立行业信用信息交换共享机制和信用调解机制等,发挥行业组织在企业征信和账款回收中的重要作用。
六是提高中小微企业诚信合规意识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
来源:国信高端智库